
曹旭云:六四35周年祭——思源之殇(上)
1、
2014 年 10 月 26 日,天气渐渐转凉。京城笼罩在外蒙古席卷而来的沙尘暴之中。天空灰暗,斑驳杂陈的树枝,在风中瑟瑟乱抖。行人的脚下及车尾卷起阵阵黄叶。
程小今昨天刚从香港回来。此番赴港,是他半个月前离开体改委某杂志主编后,携曹思源老师推介信赴港求职并拜会新老朋友,逗留一周后的折返。今日如约拜会曹老师,相当于奉命述职。他约我同行。
自去年年初曹老师罹患胃癌并做三分之二切除手术以来,我们有过几次相见。尤其是春节一晤,将两家老人约上,共叙乡情。更增添一番老亲故眷般的亲情。曹伯母 93 岁高龄,却思维敏捷。投手举足间见得出昔日妇联主任的强干和精明。我母亲虽小她一点,也有 86 岁。都是九江的媳妇,乡里乡亲。言语之间虽有一点隔音,但咬合几回后,竟十分流畅。她们中间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便交流甚欢。两家聚餐后,老人们仍执手许久,方肯散去。
又是好些天没见曹老师了。这一回,我去同仁堂选了一盒阿胶及两盒冰糖银耳。据说,阿胶伴银耳是恢复胃部功能的上好补品。小今则拿着两本刚刚在香港印好的曹老师的著作样稿。在傍晚六点钟的时候,准时赶到老师在东直门金晖嘉园的家。
曹老师金晖嘉园的家住在二楼。是将两个相邻单元套房打通,在门口装一铁栅栏而变成的独立空间。铁门内左上角一块已经挂了多年的由思源二字第一个字母演变出的 Logo 下面,是“思源破产与兼并研究所”的铜招牌。招牌微微有些锈斑和蒙尘。

这套房我很熟悉。约莫十二三年前,他们夫妇置办下这套产业时,我正办家具厂。曹老师、彬彬老师指定我来做装修,我欣然答应。原本说就免费装修,但夫妇二人一定要算钱。我才办厂,一切刚刚开始,经济上也不宽裕。便也没有多做推辞,收了 8 万块钱,给装了下来。门窗和衣柜都是那时流行的榉木板和榉木色。在老师看来,是我帮了他的大忙;而在我这里,是曹老师照顾我的买卖。
曹老师曾告诉我,购买这两套房产的资金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全国各地咨询及演讲的收入,一是当年获得过美国一届基金会的奖金,一是变卖了在玉渊潭的一套老住房。据说还有一部分按揭。
曹老师以曹大胆著称,判断市场经济在带来大量企业兴起的同时必将带来无数的企业倒闭破产。于是,创办中国首家企业破产与兼并咨询研究所。雄心勃勃,拟成为解决中国破产与兼并问题的孵化基地。拟化腐朽为神奇,从根本上遏制企业濒临破产时可能产生的巨大的社会破坏力并一举解决这个困扰企业家的老大难课题。学术研究与经营实践并行,开创一条拯救破产企业、保护私有财产的先河。事实上,以此后若干年来国内企业破产时一片狼藉的今日看过去,要是思源破产与兼并研究所还存活的话,中国不知道有多少濒临倒闭的企业可以被盘活、重获新生。
研究所开办的头几年,一上手,就是几家大型企业破产时指导性的纲领和探索性的兼并举措,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并大获成功。据国内外媒体当时的报道,依法依规让十数家千万元级别、亿万元级别的企业峰回路转、起死回生的景观,被民间和各界传为美谈。研究所锋镝所指,一时所向披靡。在上海、广州迅速办有分所。
房子分为东西两套。生意红火时,西边是办公驻地。一排炽热的日光灯下是一溜齐整的隔间办公桌,能容纳二三十号人;东边是做曹老师这位董事长的办公室、贵宾接待室兼居家之用。那时,西边那看似不起眼的一溜办公桌前,埋头坐着的,定睛看时,许多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或政经界、学术界名重一时的理论家。隔三岔五的周末,邀上京城二、三友人客串一回,就是一堂顶级的时事沙龙。在当时含美国之音的许多外媒看来,这里才是了解时下中国、了解真实样貌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
可惜,原本红红火火的买卖在 2003 年由曹老师主持召开的青岛修宪会议之后,遭到政府弹压。研究不能搞,演讲不能搞,门口 24 小时坐着个国保,生意从此一落千丈。几十号研究人员,走得只剩下几位。几个大型的破产评估、收购项目纷纷搁浅、取消。一两年后,剩下的几个人也次第离去。聪明漂亮的女秘书小翟最后一个离开。忠诚,曹老师总指着小翟对我说。小翟离去后,是家乡远房的姑娘小青接替了秘书兼照顾生活工作。小青又离去,工作及生活秘书一职就只有彬彬老师了。自己赤膊上阵,艰难时,彬彬老师给我来电询问在十里河灯具建材市场开个电源店有无可能?拟做点小买卖,补贴家用。
敲开门后,一如既往的是曹老师爽朗的笑声及欢迎之声。他晃着肥大的身躯,抓住你的双臂,牵引入座。
这时的两套房子已经合用做居家了。每次来,东边很少进去。西边原本是两房两厅,一间是小卧室,一间已经做了曹老师的办公室。由两个厅打通而成的宽敞大开间,昔日一排排隔间办公桌早就撤走,头顶一排日光灯也换成了家用吸顶灯。南边沙发,沙发北侧是一张办公、吃饭两用酱色方桌。方桌一侧顶着客厅沙发,两侧长边各三把黑色仿皮木扶手座椅,扶手也是酱木色。顶头一把主人座椅,但曹老师一般不在上首落坐,而是和客人一道坐在两侧。吃饭的时侯,彬彬老师坐在那里。
方桌的东北侧有一组电脑,秘书专用。显然,已经是彬彬老师的重地了。东侧是一排榉木橱柜。西侧一溜墙面三件物品最突出:正中是于光远先生的一首题诗。思源老师 80 年代曾是于先生门下的研究生;南边是曹老师父亲的遗像。看得出,伯父当年也一定是一介俊朗学子。去世得早,据说也就似我当时这个岁数;最突出的是北边一面大型的 V 型墙面。V 型架上格子里是曹老师的专著。这面墙,是他毕生的心血,造型也是每次都向客人自诩不已、夸耀不已、由自己设计出来的杰作。木托架上,满满当当放了他的各式著作几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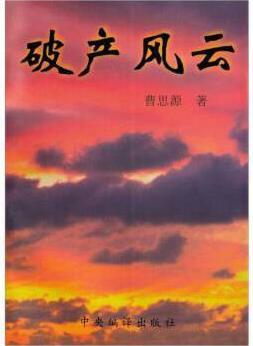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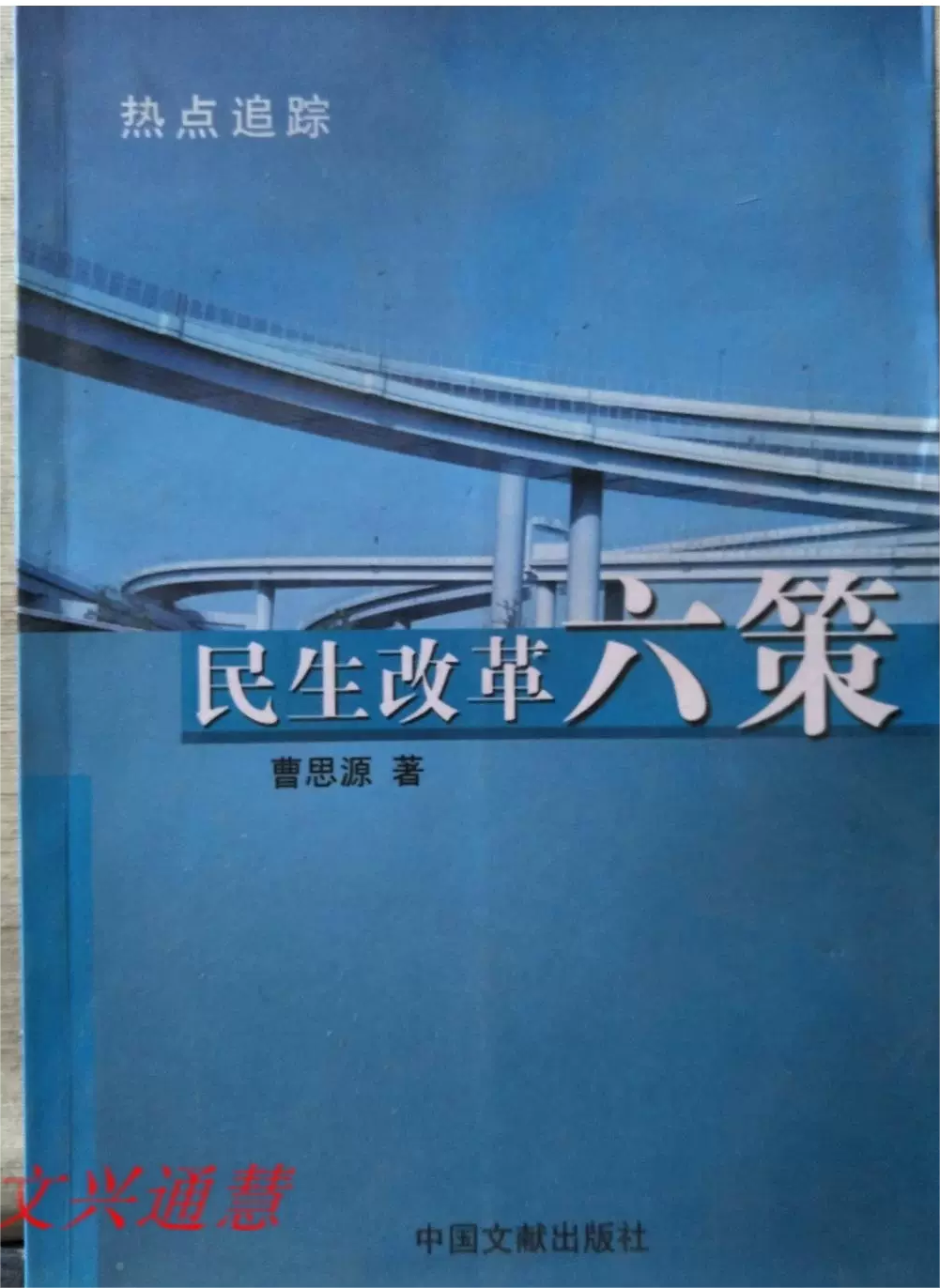
我们在方桌前落座。桌上照例是香蕉、苹果、瓜子和曹老师爱吃的水煮花生。落座、寒暄后,按照小今的提议,我们先公事后私事。所谓公事,就是此行香港的各项行程,是可以公开讲的,就到下面餐馆,一边吃一边聊;所谓私事,就是对曹老师接下来的一套《宪政修正稿大纲》编撰计划的讨论。那是要待吃完饭后,来家中密谈的。
于是,我们起身去下面餐馆。
穿过小区花园的途中,曹老师嗓门洪亮、情绪乐观:“此生此世,当做就做,当讲就讲。是值得的,老天也待我不薄。即使此时离去,也无怨无憾!哈哈。”其时,我们只当是一般的闲话。可是,当到曹老师挪着缓慢的身子,侧身走下台阶时,我才似乎猛然意识到,这是个病人。
餐厅捡一处方桌坐下,点了菜。席间小今介绍了此行香港的过程。结论是工作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确定下来的。然后,大家又讲了一些闲话。当最后问到曹老师身体时,彬彬老师抱怨,老曹太不注意了,将自己就不当个病人。一是前不久去了一趟景德镇,看望生病的二女儿。十来天,到处应酬、奔走。又因为宁波一个企业家的邀请,还转道去了一趟浙江。结果,感冒了;一是一英国朋友到来,他冒雨连夜去探访,半天打不上车。匆忙间还将脚崴了。现在连到户外运动,都没办法去。每天晚饭后走路 2000 米,是他几十年的习惯。现在,只能在屋里转圈。
你们不知道,他的病灶指标,已经从正常的 100 以下,升到 2000 了。彬彬老师最后抱怨道。“那你为什么不讲讲指标最高的是 20000 呢?嘿嘿。”曹老师反唇相讥:“你这个人讲话就是片面。”
席间,曹老师看着我强调,你们做企业的,首先是搞好经营,然后才有可能帮助到大家,去做点事情。企业家将企业做好就是最好的政治,若荒废了主业而去搞政治,那叫不务正业,也注定搞不好的。然后众人回到家中。
接下来的时间,是讨论曹老师计划依照目前中央的依宪法治国理念,拟效仿八十年代改革丛书搞一个依法治国丛书系列,并列出了目录。小今和曹老师夫妇一一推敲书目、遴选人手,讨论十分热烈。我一旁看着,心里面犯嘀咕,这个曹老师,不记教训啊。对您六、七年的钳制放松才几天呢?再说,你们又不是习中央、又没有相关人事任命和人物授权。这自费去搞,相得几何?而且,费用自何而来?当到我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时,曹老师不以为然:“我们这么多年来,所作所为,有谁指派?要说有谁指派,那就是时代指派!那就是命运指派!引用老毛的一句话,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按照他们的指派,那要等一百年!为了我们的子孙,为了千秋万代的基业,我们不能等!人家也不让我们等啊!民主之日的到来,我们一定能够看到!我把话撂在这儿。至于说到费用,我和江平已达成一致:筹划得好,这钱,还是有人愿意出的。”曹老师说到大处时,往往是激情澎湃,一泻千里。说得我只能是频频点头,心中充满愧赧。
接着,讨论进入到最关键一步,就是曹老师目前已几易其稿、并在网上被广泛浏览、广泛讨论的修正稿大纲。那是他目前及此后一个阶段的最主要的工作:“三个月,最多三个月,一把拿下!”曹老师挥挥胖拳头,嘴角上还残留着花生屑。
当夜,这个题目讨论到十一点。要不是彬彬提示,曹老师的身体需要早早休息时,大家还不愿意散去。
2、
小今离开了体改委的工作后,档期出现了空白。在大兴租住的房子也到期了。眼看入冬,即使找到新工作,也要到开春。我单位正好空出了一间房,就建议他搬过来和大家一起吃住,他欣然应允。与此同时,曹老师也不知感到林小雨谋生困难,还是听到我这边总是遭遇背叛。于是将林小雨介绍给我:江西人、赣南师院毕业,六四时因带领学生声援北京,在南昌坐牢三年、后被开除公职。到处打零工,迄今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两边一撮合,林小雨将在 11 月中旬来到公司上班。我计划让他先熟悉一下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11 月 17 日一早,得到彬彬老师的电话,说曹老师住院了。哮喘,气呼不上来。住人民医院,在重症监护室。我心里直纳闷,怎么说住院就住院呢。而且,一住就住到重症室?
当天下午,和小今第一时间来到人民医院。
在杂乱的重症监护室的过道上,看见了鼻孔里插着氧气的曹老师。他穿着条形病服,盘腿坐在装着轮子可以移动的病床上。看上去精神还行,只是头发有些蓬乱,衣衫有些不整。裤裆的纽扣,明显耷拉着。见到我们时开心不已,但从他的笑容背后见得出他的疲惫。是啊,一间不足 100 平米的房间,堆积了二三十张病床。老人、病重者、病危者挤在一间屋子。仅留出一条窄小的通道。隔着一张病床的那边,是一位看上去已奄奄一息的患者,旁边还有掩面哭泣抽搐的亲眷。周围是匆忙的大夫、慵懒的护工和满面愁容的病人家属。吵吵嚷嚷、空气污浊。就像菜市场。
我们询问了一些情况。曹老师是昨天住进来的。床铺很紧,监护室是过渡,只是一边在等床铺住院。而彬彬老师所以选择住进这家医院,是因为离家近。端个茶、送个水什么的方便。这时,彬彬不在。身边有一位请来的护工。护工是位 40 岁模样的农村妇女。见了我们,热情地招呼、让座。
来的时候已近下午五点。约莫十来分钟,就到了探视规定的时间,需要清场。曹老师利用这个时间,问了问林小雨是否能来?我告诉他,是明天的机票,明晚就能到达。接着,他询问小今与江平老师约见的情况。小今回答,是后天上午见面。他十分满意。嘱我们去忙,不要惦记,没什么大事儿。临别,小今将搁在侧案上的水果递送到他面前,我则摸出事先准备好的 5000 元现金塞在他手上。
“怎么好意思,总是用你的钱!”曹老师说完,想起身。被我按住。然后,他一往情深的注视着我们,握手而别。
翌日傍晚,小雨到达公司。鉴于次日我与小今要拜访江平老师,当晚与小雨晤面长谈。并说明我们明天不在单位,嘱其明天去看望曹老师一回。小雨去了,也是赶在那个点儿,也是只见了一面,未及详谈。只说一切还好。我们也就松懈下来。
11 月 21 日下午,正当我们惦记曹老师病况时,突然收到彬彬老师电话,说病情急剧恶化,人民医院已经不收留了,要求家属转院。他们在陈仲的帮助下,已转到了 301 医院。住在 301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翌日一早,再次与彬彬老师通话,详细了解曹老师病况。彬彬只说情况不好,病已转移到肺部及整个胸腔。而且目前也只是住监护室,未进入正式医疗救治程序,也不是住院,所以不能正常探视。301 医院病床比人民医院更加紧张,奔走都是陈仲。
“陈仲是谁?”
“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总。芳芳的同学,还是老曹的学生。”芳芳是曹老师的大女儿。至于护理,家乡景德镇准备来一位亲戚。听彬彬语气,人似极疲惫。没细说,我也不便多问。我决定第二天去 301 医院探望曹老师并全面了解一下情况。千万别出什么状况啊。
23 日下午,在凛冽的寒风中,我走进了 301 医院。去年年初,曹老师就是通过蒋彦永医生的帮助,在 301 医院查出胃癌并做的手术。凭直觉,这一次住进 301 医院的决策是对的。只是这一次是否能像上次一样化险为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我通过与陈仲通话,在西门一楼走廊尽头找到了重症监护室。当第一眼看到曹老师时,我惊呆了。
曹老师已经瘦了一圈。头发完全蓬乱,摘了眼镜布满血丝的眼睛显得出奇的大而圆。眼圈周围已布满黑色斑点,皮肤完全松弛。坐在床上,整个身子一上一下、在艰难地喘着粗气。除了身上一件典型的医院条形病服,下身显然没有穿衣,只用一条床布拢在身上。
我到达时,景德镇的亲戚、也就是芳芳的舅舅也是当天上午赶到的。听曹老师的吩咐,刚去家中拿了一点东西,这是二次返回医院。舅舅站着,手里拿着手机。显然,他们正在商量是不是与芳芳通话。
“我的手机不行。没信号。”舅舅说。
“用我的吧。”我说。
“现在几点?”曹老师问。
“下午三点。”
“她们正好是半夜。拨吧,不管了。”一边说,一边读出了芳芳的手机号码。我拨了过去。
“喂,芳芳吧?那件事不用再说了,就那样定了吧。你啊,就别想那么多。心胸要放宽大些。啊。——就这样吧。我不多说了,我呼吸困难。”啪,就挂了电话。
这么短?就这么一句?我正惊愕,忽听曹老师说:“你去吧。”再一次吩咐舅舅出门。一定是比较紧要的事儿,我想,不便多问。估计舅舅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为联络方便,便与舅舅互留了电话。并说我想要病历看看:“可以吗?”
曹老师一点头,舅舅将手提塑料袋中含病历的全部资料、费用单和户口簿等一应交给了我。这可是病人的黑匣子啊。我想。
就这一通电话,看得出,曹老师用了很大力气。
屋里只剩下他和我。我有些心疼地扯扯老师身上的床单,帮他掖紧。他半悬着坐在床沿,一脸茫然。
“你为什么不躺下呢?”我问。
“不能躺下。一躺下,就不能呼吸。”
“能睡吗?”
“坐着怎么能睡?”
“吃了点什么吗?”
“喝了点粥。”
“大小便怎么样?”
“诺。”他用指尖指了指身下。我撩开被单,是尿不湿。
“彬彬老师怎么没来?”
“她的身体一直不好。”他点着硕大的脑袋,一边艰难的呼吸一边接着说:“已经这么多天了,哎,里里外外就她一个人。”
是啊,我想到一回我母亲住在安贞医院,我家五个姊妹轮番照顾都觉得有些吃力。而且还不是什么大病。
“你现在感觉如何?”
“就是不能呼吸。”曹老师说完这句话,又一仰一合地顾着去呼吸了:“昨天还有一块靠板,今天不知为什么撤走了?”他嘟囔着。
“要不你侧身躺一会儿吧。我先与你找大夫要靠板,然后我到旁边看看你的病历?”
“好。”
我找到大夫,找来靠板。轻轻扶曹老师侧身躺下。看着他疲惫的样子,身子一起一伏艰难呼吸的样子,真不忍心再与他说话。再掖掖被单,拎着塑料袋来到了走廊。
在走廊尽头,选一处空旷的座椅,将塑料袋小心翼翼的铺开,将里边文件一一取出。这里除了一些身份资料外,更多的是人民医院和 301 医院的诊断书和收费票据,以及曹老师摘下的眼镜。我一张一张地研读,但内容的专业性太强。看了半天,一头雾水。只是从诊断书中隐约看出情况似乎已经非同小可,而这种非同小可也是用专业术语做的表述。我决定到前台问个仔细。
接待我的是一位叫刘烨的女值班主任大夫。她急切地与我介绍了情况。
“病人目前已处于癌症第四期。即俗称的癌症最末期。处在这期的病患,必须 24 小时不离家属。因为随时随地要和家属商量。可是,你们已经两天没有人在身边了。”说到这,她忽然抬头看我一眼,警觉地问:“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弟弟。”一边赶紧取出我的身份证递了过去。她接过去搂了一眼,还给我后,又接着刚才的说:“这是第一;第二,因为这不是病房,所以目前的一切治疗都没开始。都只是处于观察阶段和等候抢救状态。也就是说,目前没有固定的大夫,也不能有 24 小时的陪护和探视。因而,你们必须迅速落实病房。否则,一切都是临时性的而没有持续性和连续性。而作为这个阶段的病人,没有持续性和连续性的救治,是最危险的;第三,重症监护室的护理原则是,这个阶段,患者家属及一切人等,都只有半小时的探视和陪护时间。但是鉴于曹思源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给你们全天候的探视及守护的方便;第四,问问病人,该见什么人、想做什么事儿、想说什么话儿、想吃点什么等。尽量满足病人。”
我忽然警觉起来:“刘大夫,您说的这些,我可以不可以理解为这就是医院的濒危通知?”
“当然。”大夫的回答很迅速,也很平静。
值班主任的话,听得我阵阵背脊发凉:“那么,像这种情况,最多可以存活多久?最快又可能什么时候去世?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治愈?”
“治愈是没可能了。”大夫拢了拢手边的材料:“至于存活,两个月?一个季度?最长半年吧。——至于去世,则是随时随地的。”说完这些,她将拢起来的文材料锁进抽屉:“好了,情况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更多的时间了。——呃,请问,你既然是病人的家属,紧急情况下,能不能找您?”
“当然。”我说。
于是,她迅速翻出病人登记簿,翻到曹思源一页,让我留下电话。我瞥了一眼,在联系人一栏,已经有彬彬老师和蒋彦永大夫的签字。我就在二人后面写下手机,并签上我的名字,关系一栏写上:“兄弟。”
告别主任大夫时,我忽然握住大夫的手:“刘大夫,请问,您认识曹老师吗?”刘烨显然有些意外,摇摇头。并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您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吗?”她还是摇摇头,并礼节性的表达歉意。
“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中国人热爱的、少有的意见领袖。中国的许多大事还仗着他呢!请您务必为他多操点心。好吗?其他的事我来安排。”我尽量想说得客观些,但显然还是有些冲动。
“我会的。蒋教授也跟我做了交代。”
“谢谢。”

手拎装有病历的塑料袋准备和曹老师道别时,走过来一位年轻的女护士,向我摆摆手。示意说病人刚睡下,并附在我耳朵轻轻说:“很难得,请别打扰他。”我点点头,见他微张着嘴巴,发出轻声的呼噜。将手袋轻轻放在他床铺一侧小几上,用空杯压上,便悄悄离开了病房。
来到户外,天已黑透。一阵凉风袭来,我感觉出奇的寒冷。我立在一棵老树下,地上落满枯叶。透过树枝,是远处昏黄的夜灯。我心上一激灵,眼泪忽然涌了上来。
舅舅还没有回来。是先回去还是先在这里等候?
不行,我得赶快回去。两件事:一、将这里的真情况必须迅速告诉加拿大的芳芳;二、将这里的真实情况必须迅速告诉小今和小雨。旋即离开了医院。
